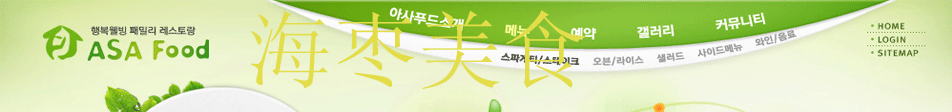|
漠南,内蒙古的别名。 在蒙古高原中间横亘着一条绵长的戈壁荒漠带,这道地理天堑以北为漠北蒙古,也称外蒙古(今日的蒙古国及俄罗斯部分地区),以南则为中国漠南蒙古或称内蒙古。 有段时间没更新了。之前写了几篇小兴安岭的游记,有点厌倦(还差两篇截稿),于是准备先写写去年秋天的内蒙之行。 说起来,这次短暂旅行缘起突然。一位搞艺术的朋友痴迷蒙古,十一期间特意从广东远赴锡林郭勒。跟着他在朋友圈里神游一番后,实在心痒,故而决定照相同路线也走一次。 他的旅行从呼和浩特开始,之后一路北上,经苏尼特右旗(西苏旗)到中蒙边境的二连浩特,继而东折苏尼特左旗(东苏旗)、阿巴嘎旗,最后终结于锡林浩特。我此行唯一不同,是在呼市与西苏旗之间加上了朱日和镇。没错,就是那个经常搞军事演习的朱日和。 高铁通车后从北京到呼市愈发便捷,全程仅需两个多小时。十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到达那里,气温已在冰点上下。当晚发往朱日和镇的火车要半夜十一点多,因此我尚有一段时间可自由支配。 这是我第三次来呼市(年游记请参阅:包头、呼市二日)。说真的,我对这里并没有什么感觉。虽然作为民族自治区首府,但满大街讲着晋语的居民让我觉得它更像一座山西城市。如果非要扯上什么民族特色,市区的回民风情则大概要比蒙古风情浓郁得多。 高铁首发站北京西直门火车站 车过八达岭,官厅水库出现在窗外 宣化古城 河北的边陲怀安县,过了这里就是内蒙了。怀来、宣化、怀安,一路上这些颇有政治意味的地名,反映的是农牧两大阵营持续两千多年的拉锯与纠葛 内蒙的边上是黄土高原向蒙古高原的过渡 蒙古高原上,先前嶙峋突兀的山峦变得愈加平缓、圆润 出了火车站,坐新近开通的地铁去内蒙古大学旁边的满都海西巷,那里据说是呼市蒙餐最为集中的街道。按照朋友推荐,选择在巷子里一间布里亚特餐厅吃晚饭。 一顿热量十足的晚饭后本以为会不惧寒冷,却没料到室外温度越发低迷。没办法,只好靠暴走来取暖。出了餐厅,去到附近一家专营蒙文出版物的网红书店打卡。在这样一个阅读变成稀缺习惯的时代,尚有人能逆潮流而动,选择在市区繁华地段开设一家小语种书店,实在让人既惊又喜。 呼和浩特火车站前的温馨提示。我的上一部手机,就是在呼市被偷走的 内亚书店位于内蒙古大学对面一家眼镜店的楼上,里面既可以看书,也可以在茶座上打发时间 书店里有一座小型蒙古包 世界各国出版的成吉思汗传记 我在书店里的收获的两册书 离开书店,时间尚早,于是便徒步走到大召附近。晚间的呼市和多数北方城市一样,商店早早关了门,街上少有行人。到了大召,发现自己有足够时间继续步行到火车站,于是沿着中山西路与锡林郭勒北路走到了车站。 检完票走向车厢途中,一位扛着大包行李的乘客在我身旁匆匆讲了一句蒙语。我没听清他说什么,但这是我在呼和浩特5个小时里听到的唯一一句蒙语(除了地铁车厢里的蒙语报站)。 火车正点发车。在清朗凛冽的夜空下,向着牧区,向着锡林郭勒,向着蒙古人众多的地方驶去。 席力图召山门墙上一则耐人寻味的温馨提示 “起床了,起床了,马上到朱日和了。” 凌晨,我被乘务员叫醒。看一眼手机,北京时间四点刚过。下了床铺,借着月光窗外已是另一派风景——浑圆的矮丘和肆意生长的芨芨草是眼前这空旷大地上唯一的注脚。低头又看了眼手机,发现一条刚刚没用看到的短信,提示我已进入鼠疫地区。 凌晨四点半到了朱日和,外面一片漆黑,气温已在冰点以下。在火车站旁找了家宾馆,继续补觉。 睁眼醒来已是早上九点多。窗外,烈日当空,蓝天下一片金色的荒芜。一夜之间就从繁忙的都市到了牧区深处,这让我有点恍惚。 朱日和位于苏尼特草原腹心,不知是否因此得名,总之它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心脏”。镇上,一条国道贯穿南北。除了部分在此吃饭、加水、补胎的过路司机,更多人只是裹挟着烟尘匆匆驶离。纵然艳阳高照,这里依旧满是寂寞与凄凉。那些想要体验黄沙小镇的人们,根本不用去到新疆、甘肃,或是美国西部,朱日和就有他们想要的一切。 我此行的目的是为了看两处古迹,一个是毕鲁图庙(完满贝乐寺),另一个是德王府。两处都在镇区郊外,包车前往是最好的方式。宾馆门口刚好聚着几位闲谈的司机,与其中一位商量好价格后,出发先去镇子南面的毕鲁图庙。 寺庙始建于年,九世班禅曾于20世纪三十年代驾临此地。清朝是藏传佛教(黄教)在蒙古地区发展的黄金时期,统治集团的大力推广是曾经骁勇善战的蒙古民族变得愈加温和、顺服的重要原因。那时的蒙古高原,是一个并不逊色于西藏的典型喇嘛王国。根据统计,清朝中期,内札萨克蒙古(涵盖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大部分地区)藏传佛教寺庙数量高达多座,喇嘛人数约15万人左右。而外蒙古喀尔喀地区在清代寺院数量也有余座。(参见:金海等著《清代蒙古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这些以今人眼光看来是宝贵文化遗产的佛寺建筑群落,在席卷全国的“文革”中几乎无一幸免,大量具有高度历史、艺术价值的文物灰飞烟灭,众多寺院被整体夷为平地。 根据资料显示,毕鲁图庙不仅是西苏旗始建年代最早的寺庙,也是目前旗内唯一幸存者。虽然此庙在十年浩劫中遭到毁灭性破坏,但大殿却因被征用为战备粮库得以保留。 从朱日和去毕鲁图庙的公路。望着眼前的旷野,想想昨天居然还在城市里,不由产生一种恍惚感 庙前的13座白塔,象征西苏旗曾经的13座庙宇 偌大的寺院,只有我一个游客 “文革”中因被当作粮库而幸存的大殿 大殿台阶上的藏文石刻 大殿后面的杂草堆中散落着许多寺庙从前的旧物 大殿的门上着锁,本以为旅行到此结束。转身的刹那,发现殿前文保碑上的朱红大字记载殿内有“艺术价值颇高”的壁画。这激起了我的兴趣,于是走到旁边的平房区,心想这里应该是教职人员居住的地方。果然,其中一个房间内有一位老大爷,正坐在屋里晒太阳。于是,我敲门入内。大爷长着鹰钩鼻的蒙古脸让我自动切换蒙语交流模式,先向他问好,之后用十分蹩脚的书面语告诉他我想进大殿参观。没想到,他竟如此痛快,二话不说拿起一串钥匙领我朝大殿走去。 途中,他还好奇地问我从哪里来,又是怎样到这里的。我如实告知,可是在解释到我是从朱日和打了个出租车到寺庙的,他却怎么也听不明白。后来一想,可能是因为我用的是“такси”(也就是taxi)这个在外蒙古更常用的说法,而当地却有另外的词汇代指出租车的缘故。 寺内的僧舍。就是在这里我找到带我进殿参观的老大爷 紧闭的殿门 让我诧异的是,殿内四壁皆白,并没有壁画。我想,大概从前是有的。后来做了社会主义的粮仓,人们自然不再需要这类的精神鸦片。 从毕鲁图庙回到镇上,去车站旁的朱日和馅饼店吃午饭。这间餐厅在这里小有名气,很多途经此地的游客还慕名而来。分别点了牛肉、羊肉和驼肉馅饼,味道还好。可能因店家使用当地特色的胡麻油烙制,刚开始吃还有点不习惯。 刚要离开寺院时,身后一声巨响,之后一朵小型蘑菇云腾空而起。后来问载我回程的司机,他说那是个铜矿 吃过午饭,司机继续载我去德王府。德王府是苏尼特末代王爷孛儿只斤·德穆楚克栋鲁普的故居。德王这个人大概算是20世纪中国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我对他的活动有个大概了解,但所知不深。我以为对于历史人物,任何非黑即白的评价都没有什么意义。判断他们的公与过,更多还要考虑当时的历史大环境,不能武断地以当下为立足点进行考量。 王府始建于年,系锡林郭勒盟第一座定居王府。府邸在建国前、后均遭受严重破坏,现存房屋大多是年起陆续修复的。旷野上,几组并列的中原汉地合院式建筑显得异常突兀,让人有种穿越时空的感觉。这些房子和同等级的北京王府相比,无论是工艺还是建筑等级,都稍显逊色。但要知道,这座德王府是修建于一个交通极不发达的年代,几乎所有建筑材料以及工匠都从内地远道而来。因此,即便是修建这样一座看起来并不是非宏伟的王府,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堪称靡费甚巨。 草原深处的德王府 王府前的草场 上图:20世纪30年代的德王府东辕门旧照 下图:修复后的东辕门 修复后的王府正门 上图:20世纪30年代从德王府正门看影壁墙 下图:现在的景象,曾经大门立柱上那些精美的木刻已经消失 王府正门前的原装上马石与石狮 王府墙根下散落的石柱础默默向游人诉说这里从前的遭遇 王府旁边不远处的一片草原上散落着许多残砖碎瓦,这里是从前九世班禅的驻锡地——当地著名的温都尔庙。遗憾的是,建国后,这里被夷为平地 温都尔庙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老照片 王府后身有一座敖包山,那里视野绝佳 从敖包山上下来,司机接我返回朱日和,在那里他已帮我联系好去往西苏旗的小车。 到达西苏旗,刚好赶上去二连浩特的车。暮色里,火车在荒原上疾驰,枯草逐渐被戈壁取代。沿途经过的车站,终于再也无法用汉语知解其义,“楚鲁图”、“郭尔奔敖包”、“夏拉哈马”、“查干特格”、“赛乌苏”...... 西苏旗火车站名叫赛汗塔拉站 年6月17日,被称为“红色文艺轻骑兵”的乌兰牧骑在西苏旗成立 苏尼特右旗去二连浩特的火车上 同车的旅客身穿印有“MONGOLIA”(蒙古)字样的夹克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 欢迎点一个“在看”? 让更多人读到。 雪饮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