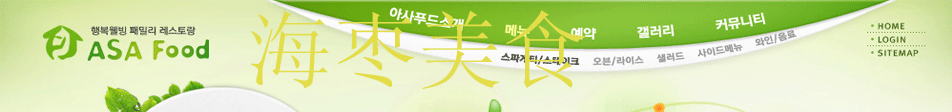|
白癜风一般出现在什么部位 http://baidianfeng.39.net/a_zzzl/150130/4569357.html 摘要 在现有中欧铁路交通格局下,土耳其“中间走廊”运输通道,相较于其北部的欧亚运输通道,其市场竞争力明显不足。但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影响力的不断拓展,面对中欧陆上集装箱运输总量的飞速增长以及中欧铁路运输主力线路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中欧班列不仅有了开行跨里海过境土耳其线路的必要,而且还增强了中土两国加强政策沟通、加快设施联通、促进贸易畅通的动力。尤其是在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新格局的背景下,正确认识和挖掘土耳其“中间走廊”的市场价值,有利于中欧班列规避风险、提升效率,促进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协调发展行稳致远。 正文 年11月首趟跨里海中欧班列成功过境土耳其抵达目的地捷克首都布拉格,标志着中欧班列“中间走廊”运输通道正式开通。这是土耳其“中间走廊”倡议和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合作的重要成果,其意义从两国及沿线部分国家运输经济部门领导人或代表齐聚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共同出席隆重的首趟跨里海中欧班列接车仪式就能体现出来。换个角度,这也意味着土耳其“中间走廊”通道正式加入中欧班列运输通道的竞争行列。 但是,新开通的土耳其“中间走廊”铁路运输通道在中欧班列过境运输中的竞争力到底如何呢?其前景如何?要分析这一问题,必须从中欧铁路交通的总体格局来看,因为当前运营的中欧班列涉及众多的运输通道和不同的运输方式,而沿线各国所牵扯的地缘政治问题也对运输线路的运行及其效率产生影响。一、土耳其“中间走廊”通道的竞争力分析 土耳其“中间走廊”通道源自土耳其外交部公开发布的文件《土耳其的多边运输政策》。泛指横穿小亚细亚、南高加索和中亚、联通土耳其和中国西部边境的多条运输道路,其中既有铁路、公路也有里海海路,既包括现有的公路、铁路、里海海运线路及其设施,也包括规划中和未来可能的地面运输线路及其设施,具有相当程度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本文主要讨论该倡议所述连接土耳其和中国西部的跨国铁路网络的既有线路,以下简称“中间走廊”。 为了探讨和比较土耳其“中间走廊”通道的竞争力,首先需要明确本文所要探究的中欧班列过境运输的几条主要通道尤其是土耳其“中间走廊”通道的基本走向。 (一)中欧班列主要运输通道 我国通常把中欧班列通道划分为东、中、西3大通道,从欧亚大陆整体视角来看,我国国内开行过的众多中欧班列线路,包括试验线路都可归结到4条欧亚主要通道上,这些运输线路当前主要依托2个大陆桥,构成了以中欧班列为主要运输形式、以集装箱为主要运输载体,沟通中国与欧洲两个大市场、带动沿线国家过境运输和经济贸易发展的货运物流服务网络。 这4条欧亚大通道从北到南分别是第一亚欧大陆桥的跨西伯利亚走廊、新亚欧大陆桥、跨里海中亚高加索走廊(“中间走廊”通道)和中亚—西亚走廊。 跨西伯利亚走廊:该通道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到鹿特丹全长约千米。中欧班列依托西伯利亚大铁路主要分为两条线路:东线是从哈尔滨或经哈尔滨出发,从满洲里出境,经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铁路经莫斯科、布列斯特、华沙到德国汉堡、柏林或杜伊斯堡的线路;西线是从天津或北京出发,从二连浩特出境,走乌兰巴托、乌兰乌德,接入西伯利亚大铁路、莫斯科、布列斯特、华沙到德国的线路。这条货运大通道以满洲里出境线路为主。 新亚欧大陆桥:这是目前中欧班列跨境运输的主线路。该线路从连云港到鹿特丹全长约千米。它依托我国陇海兰新线分成南北两条线,北线囊括了大量中国中西部城市始发从新疆阿拉山口出境,经阿克斗卡、卡拉干达、彼得罗巴甫尔,向北接入俄铁,经莫斯科、布列斯特、华沙到德国的线路,南线包括从霍尔果斯出境,经阿拉木图、奇姆肯特、克孜勒奥尔达、阿克托别、奥伦堡、布列斯特等城市到德国的线路。 跨里海中亚高加索走廊:该通道即土耳其“中间走廊”。从连云港到鹿特丹全程约千米,该线前半段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分成北、中、南3条线,其北线从中国中西部城市始发经阿拉山口出境,经热兹卡兹干、沙尔卡尔、别伊涅乌到阿克套或库里克港,乘火车轮渡过里海到阿塞拜疆巴库阿拉特港;中线从霍尔果斯出境、经阿拉木图,在奇姆肯特向北,至沙尔卡尔向西到阿克套或库里克港乘火车轮渡跨里海到阿拉特港;南线从霍尔果斯出境,经阿拉木图,在奇姆肯特向南,经塔什干、撒马尔罕、布哈拉、阿什哈巴德到土库曼斯坦巴什港,乘火车轮渡到阿拉特港。这3条线在巴库阿拉特港汇合成一条线,走巴库—第比利斯—卡尔斯铁路,横穿土耳其前往欧洲。因地缘政治等方面的原因,目前跨里海中欧班列只能采用该走廊的中、北两条线路。 中亚—西亚走廊:此线从连云港到鹿特丹全程约千米,它也分为南北两条线路。传统线路是南线,它从霍尔果斯出境后,走阿拉木图、奇姆肯特、塔什干、撒马尔罕、布哈拉,到土库曼斯坦捷詹后转向南行,经谢拉赫斯进入伊朗,走马什哈德、德黑兰、大不里士,经凡城火车轮渡,转安卡拉、伊斯坦布尔前往欧洲;北线是近年建成的新线,它从阿拉山口或霍尔果斯出境,在哈萨克斯坦西部别伊涅乌转乌津,从波拉沙克进入土库曼斯坦,到卡赞吉克后,或走英奇博荣到伊朗戈尔甘、德黑兰,或走阿什哈巴德、捷詹、谢拉赫斯到德黑兰。受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目前中欧班列并未采用这条赴欧线路,而少量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的班列,其采用的也是北线路。 值得注意的是,跨里海中亚高加索走廊和中亚—西亚走廊铁路线路与欧洲TRACECA项目的部分线路重叠。 (二)影响土耳其“中间走廊”通道竞争力的要素分析 为了探讨“中间走廊”通道在中欧班列过境运输方面的竞争力,我们选择了影响托运人选择中欧班列不同线路的主要因素进行比较,这包括运输距离、运输费用、运输时长这3个主要考虑因素以及与运输效率相关的基础设施状况、途经国家数量、运输方式、换装次数、地理气候条件与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 第一,运输距离。土耳其“中间走廊”的3条线路在中欧班列的运输距离上并不占优势,它们并不是目前中欧班列跨境运输距离最短的线路。 拿中欧班列典型的几条主要线路进行比较,走第一大陆桥的哈尔滨—满洲里—汉堡班列全程千米、走新亚欧大陆桥的兰州—阿拉山口—汉堡班列全程千米,即使是渝新欧重庆—阿拉山口—杜伊斯堡全程也只有千米,而从西安出发走“中间走廊”距离较短的北线跨里海到布拉格全程就达千米,这还只是到中欧的布拉格,而不是中欧班列跨境运输的主要目的地德国柏林、汉堡和杜伊斯堡(参见表1)。 因此,客观地说,在当前的中欧班列跨境运输格局下,土耳其“中间走廊”运输通道相较于新、旧大陆桥,它目前在运输距离上并没有优势。 第二,运输费用。大约占到铁路运输总成本的三分之二。依据俄铁规定,从阿拉山口入境的运费费率为0.7美元/FEU[3]·千米,从满洲里入境的运费费率为0.4美元/FEU·千米。简单换算一下,从满洲里到汉堡的基本运费约为美元/标箱,从阿拉山口—汉堡的基本运费约为美元/标箱,[4]即使是常态化运营的重庆—阿拉山口—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当前的全程运费也只有美元每40英尺长箱,简单换算一下全程约美元/标箱,而年从连云港经“中间走廊”到伊斯坦布尔的运费协议价为美元/标箱。相似地,沿乌鲁木齐—阿克套—里海—巴库—波季—欧盟一线的运费约美元/标箱,也就是说“中间走廊”的运费明显高于跨西伯利亚走廊和新亚欧大陆桥,更是远远高于海运(不同目的地运费情况参见表2)。 第三,运输时长。从当前中欧各班列的运输时长上看,中欧班列与海运相比具有很大的时间优势,节约运输时间一半以上,但就中欧班列各条线路进行比较,则土耳其“中间走廊”与新大陆桥和第一大陆桥相比,在运行时间上仍处于劣势(参见表1)。 据报道,年从阿拉山口出境到白俄罗斯布列斯特的铁路运营时长已经稳定在6天左右,重庆、成都、西安、郑州发车经阿拉山口出境前往欧洲的中欧班列的全程时长常态化稳定在12天左右。为了与阿拉山口竞争,俄罗斯提高了跨西伯利亚铁路的运营速度,年起中欧班列横穿俄罗斯也只要6—7天。但新开通的西安经“中间走廊”到布拉格线路根据国内报道全程耗时共15天,而实际运行了18天,这还是在沿线国家高度重视和协调下的首次班列的运行情况。 第四,基础设施状况。总体来看,经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耳其赴欧的各条线路的基础设施状况都有待提高,这是影响中欧班列稳定运行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线路基础设施状况不佳表现经以下几方面:其一线路老化。俄哈等国不少线路还是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老基础设施和设备,尤其是在中亚地区,已经非常落后和老化。即使是在条件相对较好的哈萨克斯坦,不少线路包括新建线路仍是单线铁路,像重点口岸站多斯特克,其接运能力严重不足,造成我国出口货物经常停装限装,长时间滞留。其二是运能不足。俄铁跨西伯利亚走廊理论上的集装箱中转容量为25万标箱/年,当前其利用率已达%,哈萨克斯坦的集装箱运输总量总共只有25万标箱/年,其中过境运输就占了80%,而“中间走廊”的枢纽阿塞拜疆的阿拉特港,其设计的集装箱最大吞吐量仅有5万标箱。据报道,年前7个月阿克套港的集装箱运量超过了12吨(约合—标箱),是去年全年的5倍多,增长迅猛,按此增速,该线路的瓶颈状况很快就会显现。其三是集装箱化水平低。俄罗斯的集装箱化水平低于中国美国3倍多,哈萨克斯坦的状况又远低于俄罗斯,而哈萨克斯坦的基础设施状况在中亚地区总体上还是处于领先水平的。其四是改造升级困难,投资费用高昂。据估计,对跨西伯利亚走廊进行现代化改造需要投资20亿美元,改造新亚欧大陆桥需60亿美元,但土耳其“中间走廊”的关键工程、耗时10年之久的巴库—第比利斯—卡尔斯铁路已知的投资额就超过了34亿美元,哈萨克斯坦新建的东西干线热兹卡兹干—别伊涅乌段全程千米,耗资.9亿坚戈(合27.55亿美元),而跨西伯利亚走廊、新亚欧大陆桥以及土耳其铁路的更新规模实际上会远超以上两项工程。 此外,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苏联国家相比,土耳其的铁路基础设施状况还要更复杂一些。当前土耳其既有少量新建设的现代化线路,如安卡拉—伊斯坦布尔高铁,也有大量建于共和国早期的铁路,甚至还有不少建于帝国时代的老旧线路,其中一个明显的问题是电气化不足。更主要的是,长期以来土耳其国内运输以公路运输为主,其铁路运输只占全国运输总量的4%左右。除了土耳其人出行方面的传统习惯,这种情况与其铁路基础设施不佳、铁路运输速度慢、准点率低、线路运营规划刻板、管理调度水平、托运便利程度不高、冷链系统不足等等不无关系。因而,从根本上讲,改善老线路、兴建新线路、提升铁路运营管理现代化水平仍是土耳其需要解决的一个长期的任务。 因此,在俄罗斯将其跨西伯利亚铁路的运营速度提升到90—千米的时速时,土耳其国内的不少线路的运营速度还停留在40千米/小时的水平上。 第五,途经国家数量。列车过境他国要接受他国管辖,必须满足过境国的法律要求,因此,鉴于不同国家的法律差异尤其是运输法规的差异,过境国数量也是影响中欧班列运行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他人研究,因为在口岸通关、检验检疫、换装乃至压货、甩车等问题,中欧班列在口岸的滞留时间,占全程运行时间的30%左右。 明显地,走跨西伯利亚走廊的中欧班列其过境国最少,跨境次数少,无论是从满洲里还是绥芬河出境,前往德国只需经过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5个国家,跨境4次。而新亚欧大陆桥也只经过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6个国家,跨境5次。但是取道“中间走廊”通道,如果其目的地是德国柏林或汉堡的话,走“中间走廊”中线和北线一共要经过中国、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土耳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德国11个国家,跨境10次。而走南线则要增加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两国,并且因为铁路走向问题,其间还要再入境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各一次。事实也是如此,首次跨里海中欧班列“长安号”是截至目前开行的所有中欧班列中,途经国家最多、运输方式最全的线路,全程共经过了10个国家。 第六,运输方式。这分为单式运输和多式联运方式。跨西伯利亚走廊和新大陆桥只有铁路运输这一种运输方式,除了因轨距不同换车底,中途无须变换运输方式,而“中间走廊”无论北中南3条线都绕不开里海,必须实行铁海联运,用火车轮渡过里海,一共需要进行两次转换。其间不仅要受港口的转换效率的影响,还要受阿塞拜疆里海航运公司运能和班期以及天气条件的制约。这种情况在中亚—西亚走廊也同样存在,列车从伊朗进入土耳其后,在凡城需要乘火车轮渡通过凡湖,进行两次转换,然后才能继续前行。 第七,换轨次数。技术层面因铁路轨距不同需要换装,因为苏联地区为毫米宽轨,而中国、土耳其、伊朗及欧洲大部为毫米标准轨,因此,除目的地为苏联的俄罗斯、白俄罗斯、中亚、高加索等国家以及蒙古之外的中欧班列,无论采用哪条线路都要进行2次转换,走“中间走廊”通道也不例外。边境换装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工作,它直接增加了货物的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在我国阿拉山口对面的多斯特克,由于集装箱专用平车短缺,列车换装不便经常造成货物滞留,且由于哈方铁路线路为单线,这更增加了调运困难。而在欧盟边境,随着中欧班列的迅速增加,白俄罗斯和波兰边境的布列斯特和马拉舍维奇过于繁忙造成货物拥堵积压,突显出其换装能力已然不足,与此相反的是,格鲁吉亚的阿哈尔卡拉基换装点和BTK线路的过货量则远低于设计运能。自年BTK线路开通运行以来,年该线共运送集装箱标箱,年运送了标箱。尽管这显示出在“中间走廊”线路上的集装箱运输还存在大量的资源冗余,但这并不能消除换装给铁路运输造成的额外时间成本与运输成本。 第八,调度管理水平。这主要涉及相关的人才和技术储备,在这方面俄罗斯具有明显的优势。早在年4月俄铁曾经试验将其西部卡卢加地区的一批集装箱列车以当时创纪录的7天时间快速通过俄罗斯联邦,以此展示出俄铁特事特办、快速规划搭建铁路快速直通通道的实力,由此也不难看出,这也是年起俄罗斯铁路公司能够将经由第一大陆桥横跨俄罗斯的中欧班列全程运营时间缩短至6—7天的重要原因。更重要的是,为了提高竞争力,俄铁不断地在车底调配、开行计划保障、铁路运费下浮等方面给予支持。而在这方面,“中间走廊”沿线的其他国家,包括哈萨克斯坦、土耳其还需要不断加大对其国内相关人才、技术、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中间走廊”通道的通行效率和市场竞争力,才有可能充分发挥乃至进一步提升其铁路资源的实际利用率和潜力,从而创造其期望中的经济效益。 第九,沿线气候条件。这对某些商品,尤其是农产品运输是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总体来看,“中间走廊”和中亚—西亚走廊处于北纬45度以南,其气候条件相对温和,冬季运输条件明显优于跨西伯利亚走廊和新亚欧大陆桥,但需要考虑的是土耳其东部山区、哈萨克斯坦和我国北疆地区的冬季也同样十分寒冷,通过“中间走廊”运输同样也需要增加保温措施从而提高了运输成本。 第十,地缘政治因素。这一因素对跨境交通运输来说,至少在特定时间内,除了绕行,基本上无解。地缘政治因素包括某些国家的国内冲突、地区冲突和大国博弈,典型的例子如年土耳其单方面修改海峡通行条例和年欧盟因为克里米亚问题制裁俄罗斯,从而招致俄罗斯禁止欧洲农产品通过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领土的报复措施。因此,鉴于哈萨克斯坦是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的重要成员,在俄罗斯反制欧盟制裁的情况下,即使使用“中间走廊”运输的中欧班列也无法运输欧洲相关农产品来华。这从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我们对中吉乌铁路等线路的规划建设风险问题的认识。 总结一下,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除了气候条件,土耳其“中间走廊”相较于其北部的两条欧亚运输通道,在中欧班列过境运输所涉及的几乎所有因素中都处于劣势。换句话说,在当前中欧班列运输格局下,如果没有其他重大因素变化或外力推动,土耳其“中间走廊”的现有竞争力相对跨西伯利亚走廊和新亚欧大陆桥都不具有优势。 二、中欧班列通道面临的问题与“中间走廊”的机遇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整体推进和中欧班列的极速发展,中欧班列原有线路所固有的问题逐步显现出来,一方面形成了中欧班列快速发展的瓶颈和困难;另一方面也给中欧班列拓展渠道、求新求变提供了动力,给包括土耳其“中间走廊”在内的中欧之间的道路联通带来了新机遇,增强了其竞争力。 当前运营的中欧班列线路面临的问题及其带给“中间走廊”的机遇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运输通道和过境点过于集中,亟须改善联通性 从欧亚大陆的整体视角,现有中欧班列线路的走向及其瓶颈几乎一目了然,其地理分布特点也十分突出:一是现有中欧班列线路在我国的出境点和欧盟的入境点高度集中,尤其是后者;二是现有中欧班列线路对俄铁、哈铁的依赖度非常高,并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一格局都难以改变。 中欧班列在我国的出境点主要是满洲里、二连浩特、阿拉山口和霍尔果斯,其中满洲里和二连浩特的出境线路高度依赖俄铁跨西伯利亚大铁路,西部出境点受地理条件制约,高度集中于新疆一隅的阿拉山口和霍尔果斯,其出境线路高度依赖哈萨克斯坦铁路公司。而无论新亚欧大陆桥、跨里海“中间走廊”还是中亚—西亚走廊,亦即,在当前条件下,即使是取道土耳其“中间走廊”和中亚—西亚走廊的中欧班列,也无法绕开哈萨克斯坦和中哈边境的2个铁路口岸。 而在另一边,中欧班列在欧盟边境的入境点集中在白俄罗斯的布列斯特,其集中度高达90%—95%,尽管尚存从俄罗斯波罗的海飞地港口少量转运的通道,但难以改变当前中欧班列对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铁路基础设施高度依赖、对布列斯特入境点高度依赖的事实。此外,不可否认,布列斯特入境点也是经过中欧班列长期实践证明的最优选择。 因此,在中欧班列跨西伯利亚通道和新亚欧大陆桥入境欧盟几乎必经白俄罗斯布列斯特的情况下,新增加的土耳其“中间走廊”通道及土欧卡帕库尔入境点在事实上改善了中国对欧盟贸易的联通性和过货能力,至少是在物理上增加了这种改变的潜力。尽管这条线路并不完美,也存在着大量瓶颈和不确定性,诸如里海天气的影响、里海航运的运能和效率、土耳其马尔马拉海底隧道和边陲小城卡帕库尔的通行能力,以及沿线国家间的地缘政治问题和考量等等,另外还有一个居高不下的运价。 (二)沿线铁路基础设施不堪重负,亟须增强分流能力 中欧班列从年3月19日渝新欧首发至今已逾9年,截至年底累计开行列,年开行数量也从年最初的17列增长到年的列。尤其是自年以来,开行数量可以说是实现了井喷式增长,年开行了列、年列、年列、年列。而年1—5月份,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中欧班列还是累计开行了列,发送货物35.5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了28.5%和32%,其中5月份开行列,单月开行次数首次破千,发送货物9.3万标箱,同比增长43%和48%。 这一成绩确实喜人,但喜中有忧,这几年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和运量的急剧增长,也给沿线铁路基础设施造成很大压力,其直接后果就是效率降低。年中欧班列渝新欧全程运行时间曾缩短到11天,但现在因为拥堵而大幅延宕。特别是位于瓶颈的白俄罗斯布列斯特和波兰马拉舍维奇换装点,其宽轨设施屡次达到了极限使用状态,而场站的扩容建设仍在进行中。即使是我国国内重点建设的主要出境口岸阿拉山口和霍尔果斯,在今年疫情的影响下,猛增的班列数量也让口岸应接不暇。 因此,在不断提升瓶颈口岸的过境能力的同时,通过货物分流来提高中欧班列的运行效率,已是形势所迫,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而遍观欧盟边境可供选择的入境点,包括黑海、地中海的海路入境点,综合考虑沿线地区的地缘政治限制,在不增加现有线路基础设施压力的情况下,土欧边境的卡帕库尔就是当前最好的选择。 这个“最好”的选择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卡帕库尔出境点两边的土耳其、保加利亚(欧盟)和中欧班列跨里海沿线国家国内政治稳定,沿线国家间没有大的地缘政治纠葛,沿线国家尤其是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土耳其等主要国家积极推动过境运输发展和运输便利化。众所周知的是,和平和稳定是发展交通提振经济最关键、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所涉国家利益的一致性更是协调与合作的利好因素;另一方面,“中间走廊”通道现存的问题主要是监管、通关、信息交互、过境费用等技术性问题和改善、完善基础设施等发展性的问题,不存在不可解决的冲突和矛盾,在大目标基本一致的情况下,经过沿线各个国家的共同努力,这类问题都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毕竟一条稳定、安全、便捷的欧亚贸易运输通道符合沿线各国的共同利益和期待,而这种合作共赢的前景就是对该线路和卡帕库尔入境点的最有力支持。 (三)运输目的地过于集中,亟须拓展新的运输市场 中欧班列虽然现有近70条线路,但在欧盟的目的地绝大部分集中在德国及其附近,在欧(盟)目的地过于集中是造成中欧班列现存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种情况也是欧盟内部对华贸易发展不平衡在铁路货物运输上的一个反映。 虽然近些年中欧贸易总体上呈上升势头,但年以来的中欧双边贸易数据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中欧贸易额增长缓慢,甚至时有反复;二是双边贸易的发展,距离习近平总书记年4月1日访欧时提出的到年中欧贸易总额达到00亿美元的宏伟目标还有不小差距(参见表3)。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首先是欧盟限制对华高技术出口以及欧盟中低技术产品对华失去竞争优势造成欧盟对华出口疲软。其次也与欧盟内部对华贸易国别不平衡有很大关系,少数几个成员国就占据了欧盟对华贸易的大部分份额。 根据欧洲统计局和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以年为例,中国和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货物贸易经济体。年中国是欧盟商品出口的第3大目的地(占比9%)和商品进口的最大来源国(占比19%),相应地,欧盟向中国出口亿欧元,自中国进口亿欧元。但从欧盟27国内部来看,年仅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4国自中国进口就占当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总额的63.2%,其对中国出口占当年欧盟对中国出口总额的72.8%。其中,德国是欧盟中从中国进口的第2大国(占比21.3%)和最大的对华商品出口国(占比48.6%),其对华货物贸易总额.55亿欧元在欧盟27国对华亿欧元的贸易总额中占比高达30.9%(以上数据依据欧盟统计局数据计算得出)。从中不难看出,德国对华贸易总量大、在欧盟对华贸易中比重高是中欧班列赴德的一个重要原因。换个角度,这也表明多数欧盟成员国对华贸易发展还极不充分,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参见表4)。 有鉴于此,尽管中欧贸易和中德贸易关系稳固,但要想进一步提升中欧贸易水平,达到00亿美元的年贸易目标,就必须寻找新的增长点。因此,在“一带一路”迅猛发展的今天,尤其是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农产品进口大国的情况下,拓展对东南欧等欧洲其他地区国家的经济关系就显得十分必要,有利于平衡中欧贸易减少贸易摩擦、平衡欧洲内部的对华贸易、促进东南欧经济的发展乃至扩大“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力和效益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而随着我国与东南欧、东欧经贸关系的发展,跨里海过境通道即“中间走廊”通道的竞争力也会逐步增强,其市场份额将会稳步提高。从这个角度和长远来看,中欧班列开通跨里海过境土耳其连接东南欧线路具有一定的经济性、前瞻性和比较光明的发展前景。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整体推进和中欧班列的极速发展,中欧班列原有线路所固有的问题逐步显现出来,一方面形成了中欧班列快速发展的瓶颈和困难;另一方面也给中欧班列拓展渠道、求新求变提供了动力,给包括土耳其“中间走廊”在内的中欧之间的道路联通带来了新机遇,增强了其竞争力。 当前运营的中欧班列线路面临的问题及其带给“中间走廊”的机遇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运输通道和过境点过于集中,亟须改善联通性 从欧亚大陆的整体视角,现有中欧班列线路的走向及其瓶颈几乎一目了然,其地理分布特点也十分突出:一是现有中欧班列线路在我国的出境点和欧盟的入境点高度集中,尤其是后者;二是现有中欧班列线路对俄铁、哈铁的依赖度非常高,并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一格局都难以改变。 中欧班列在我国的出境点主要是满洲里、二连浩特、阿拉山口和霍尔果斯,其中满洲里和二连浩特的出境线路高度依赖俄铁跨西伯利亚大铁路,西部出境点受地理条件制约,高度集中于新疆一隅的阿拉山口和霍尔果斯,其出境线路高度依赖哈萨克斯坦铁路公司。而无论新亚欧大陆桥、跨里海“中间走廊”还是中亚—西亚走廊,亦即,在当前条件下,即使是取道土耳其“中间走廊”和中亚—西亚走廊的中欧班列,也无法绕开哈萨克斯坦和中哈边境的2个铁路口岸。 而在另一边,中欧班列在欧盟边境的入境点集中在白俄罗斯的布列斯特,其集中度高达90%—95%,尽管尚存从俄罗斯波罗的海飞地港口少量转运的通道,但难以改变当前中欧班列对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铁路基础设施高度依赖、对布列斯特入境点高度依赖的事实。此外,不可否认,布列斯特入境点也是经过中欧班列长期实践证明的最优选择。 因此,在中欧班列跨西伯利亚通道和新亚欧大陆桥入境欧盟几乎必经白俄罗斯布列斯特的情况下,新增加的土耳其“中间走廊”通道及土欧卡帕库尔入境点在事实上改善了中国对欧盟贸易的联通性和过货能力,至少是在物理上增加了这种改变的潜力。尽管这条线路并不完美,也存在着大量瓶颈和不确定性,诸如里海天气的影响、里海航运的运能和效率、土耳其马尔马拉海底隧道和边陲小城卡帕库尔的通行能力,以及沿线国家间的地缘政治问题和考量等等,另外还有一个居高不下的运价。 (二)沿线铁路基础设施不堪重负,亟须增强分流能力 中欧班列从年3月19日渝新欧首发至今已逾9年,截至年底累计开行列,年开行数量也从年最初的17列增长到年的列。尤其是自年以来,开行数量可以说是实现了井喷式增长,年开行了列、年列、年列、年列。而年1—5月份,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中欧班列还是累计开行了列,发送货物35.5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了28.5%和32%,其中5月份开行列,单月开行次数首次破千,发送货物9.3万标箱,同比增长43%和48%。 这一成绩确实喜人,但喜中有忧,这几年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和运量的急剧增长,也给沿线铁路基础设施造成很大压力,其直接后果就是效率降低。年中欧班列渝新欧全程运行时间曾缩短到11天,但现在因为拥堵而大幅延宕。特别是位于瓶颈的白俄罗斯布列斯特和波兰马拉舍维奇换装点,其宽轨设施屡次达到了极限使用状态,而场站的扩容建设仍在进行中。即使是我国国内重点建设的主要出境口岸阿拉山口和霍尔果斯,在今年疫情的影响下,猛增的班列数量也让口岸应接不暇。 因此,在不断提升瓶颈口岸的过境能力的同时,通过货物分流来提高中欧班列的运行效率,已是形势所迫,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而遍观欧盟边境可供选择的入境点,包括黑海、地中海的海路入境点,综合考虑沿线地区的地缘政治限制,在不增加现有线路基础设施压力的情况下,土欧边境的卡帕库尔就是当前最好的选择。 这个“最好”的选择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卡帕库尔出境点两边的土耳其、保加利亚(欧盟)和中欧班列跨里海沿线国家国内政治稳定,沿线国家间没有大的地缘政治纠葛,沿线国家尤其是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土耳其等主要国家积极推动过境运输发展和运输便利化。众所周知的是,和平和稳定是发展交通提振经济最关键、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所涉国家利益的一致性更是协调与合作的利好因素;另一方面,“中间走廊”通道现存的问题主要是监管、通关、信息交互、过境费用等技术性问题和改善、完善基础设施等发展性的问题,不存在不可解决的冲突和矛盾,在大目标基本一致的情况下,经过沿线各个国家的共同努力,这类问题都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毕竟一条稳定、安全、便捷的欧亚贸易运输通道符合沿线各国的共同利益和期待,而这种合作共赢的前景就是对该线路和卡帕库尔入境点的最有力支持。 (三)运输目的地过于集中,亟须拓展新的运输市场 中欧班列虽然现有近70条线路,但在欧盟的目的地绝大部分集中在德国及其附近,在欧(盟)目的地过于集中是造成中欧班列现存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种情况也是欧盟内部对华贸易发展不平衡在铁路货物运输上的一个反映。 虽然近些年中欧贸易总体上呈上升势头,但年以来的中欧双边贸易数据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中欧贸易额增长缓慢,甚至时有反复;二是双边贸易的发展,距离习近平总书记年4月1日访欧时提出的到年中欧贸易总额达到00亿美元的宏伟目标还有不小差距(参见表3)。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首先是欧盟限制对华高技术出口以及欧盟中低技术产品对华失去竞争优势造成欧盟对华出口疲软。其次也与欧盟内部对华贸易国别不平衡有很大关系,少数几个成员国就占据了欧盟对华贸易的大部分份额。 根据欧洲统计局和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以年为例,中国和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货物贸易经济体。年中国是欧盟商品出口的第3大目的地(占比9%)和商品进口的最大来源国(占比19%),相应地,欧盟向中国出口亿欧元,自中国进口亿欧元。但从欧盟27国内部来看,年仅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4国自中国进口就占当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总额的63.2%,其对中国出口占当年欧盟对中国出口总额的72.8%。其中,德国是欧盟中从中国进口的第2大国(占比21.3%)和最大的对华商品出口国(占比48.6%),其对华货物贸易总额.55亿欧元在欧盟27国对华亿欧元的贸易总额中占比高达30.9%(以上数据依据欧盟统计局数据计算得出)。从中不难看出,德国对华贸易总量大、在欧盟对华贸易中比重高是中欧班列赴德的一个重要原因。换个角度,这也表明多数欧盟成员国对华贸易发展还极不充分,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参见表4)。 有鉴于此,尽管中欧贸易和中德贸易关系稳固,但要想进一步提升中欧贸易水平,达到00亿美元的年贸易目标,就必须寻找新的增长点。因此,在“一带一路”迅猛发展的今天,尤其是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农产品进口大国的情况下,拓展对东南欧等欧洲其他地区国家的经济关系就显得十分必要,有利于平衡中欧贸易减少贸易摩擦、平衡欧洲内部的对华贸易、促进东南欧经济的发展乃至扩大“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力和效益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而随着我国与东南欧、东欧经贸关系的发展,跨里海过境通道即“中间走廊”通道的竞争力也会逐步增强,其市场份额将会稳步提高。从这个角度和长远来看,中欧班列开通跨里海过境土耳其连接东南欧线路具有一定的经济性、前瞻性和比较光明的发展前景。 (四)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大,亟须分散风险 中欧班列两条主通道西段所穿越的是当今世界上地缘政治问题最为突出的地区之一,俄美、俄欧和苏联部分国家间的地缘政治冲突可能缓和,但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消失,在某些情况下还会激化。 目前,俄乌、俄欧因为年克里米亚问题造成的制裁与反制裁斗争尚未解决,最近又因白俄罗斯总统选举反对派拒绝承认大选结果而引发以俄白为一方、以欧美与白反对派为另一方的新一轮国际角力,造成白俄罗斯政局和社会的持续动荡。在这轮博弈中,不仅欧美大国和俄罗斯卷入其中,白俄罗斯的邻国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也公开、强力支持白俄罗斯反对派,直接干预白俄罗斯内政,向卢卡申科政府施压。而就在普京就白俄罗斯危机频繁与欧洲领导人交涉、局势有所缓解之际,德俄、欧俄关系又因俄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利内突然蹊跷“中毒”而僵持不下。 截至目前,白俄罗斯的这场政治危机何时结束、如何结束迄未可知,但白俄罗斯社会的持续动荡肯定会对中欧班列的正常运营带来负面冲击,尤其是在大多数中欧班列必须经过白俄罗斯布列斯特的情况下。反过来,这种情势迫使中欧班列必须考虑分散运营风险,从而给绕过俄、白的“中间走廊”线路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三、“一带一路”框架下土耳其“中间走廊”通道发展前景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发现,在现有中欧铁路交通格局下,土耳其“中间走廊”运输通道,相较于其北部的两大欧亚运输通道,在中欧班列跨境运输所涉及的几乎所有重要因素中都处于劣势,其市场竞争力明显不足。但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影响力不断拓展的情况下,随着中欧陆上集装箱运输总量的飞速增长以及中欧铁路运输主力线路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中欧班列不仅有了开行跨里海过境土耳其线路的必要,而且还进一步增强了“中间走廊”沿线国家,尤其是中土两国加强政策沟通、加快设施联通、促进贸易畅通的动力。 首先,在倡导推动各国,尤其是亚欧间的互联互通方面,土耳其的“中间走廊”倡议和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高度契合的,而促进中欧班列跨境运输是中土两个倡议对接与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土耳其方面热切期盼的合作项目。 而对于铁路运输和建设这样的基础设施项目,没有相关国家政府的支持和推动是不可相像的。土耳其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最早的支持者之一,两国政府长期保持着高层政策沟通。早在年12月,时任土耳其外长达武特奥卢就表示,土耳其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天然支持者和参与者,土方愿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当中。年11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公开表示全力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愿在此框架内不断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水平。[24]年11月安塔利亚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两国签署了《协调“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间走廊”倡议的谅解备忘录》,为推进两国各领域合作提供了重要政策支持。经过积极协作,年5月13日,埃尔多安总统来华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土耳其共和国政府国际道路客货运输协定》,明确中土两国运输车辆可到达对方领土和过境对方领土,并允许两国运输车辆从第三国进出对方领土,从而扫清了中欧班列土耳其跨境运输的法律障碍,推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 第二,“一带一路”倡议也助推了土耳其“中间走廊”倡议所倡导的与其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最典型的例子是建设长达10年之久的巴库—第比利斯—卡尔斯铁路项目,这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土耳其三国合作的重点工程,初始目的是让阿塞拜疆、格鲁吉亚通过土耳其与欧洲连接到一起。但其实施过程也是一波三折,困难重重,是我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及其后“一带一路”倡议给这项三国合作项目展示了新的前景并重新注入了动力,从而将巴库—第比利斯—卡尔斯铁路建成了沟通中亚、东亚和西亚、欧洲的重要桥梁。 重要的是,跨里海中欧班列是土耳其及沿线国家热切期盼的合作项目,沿线国家渴望中欧班列跨境运输能够带动他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首趟跨里海过境土耳其中欧班列的开行,是中土两国及沿线国家积极推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的结果,也是土耳其“中间走廊”倡议和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合作的重要成果,完全符合沿线国家的利益和期待。而为了带动并进一步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贸易发展、推进中土两个倡议的合作,中土两国有关部门还需紧紧把握住当前出现的新机遇,继续通力协作,为跨里海过境土耳其中欧班列的常态化运营扫清各种壁垒和障碍,共同造福两国和沿线各国人民。 另一方面,还应该看到,要进一步提升“中间走廊”通道的市场竞争力,正确认识和挖掘其市场价值仍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当前,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双循环”,形成了立足国内市场,让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相互促进的新格局。这为中欧班列突破现有瓶颈、拓展服务新市场、促进联通国内国外两个循环创造了更大的政策空间。而在这其中,“中间走廊”与中欧班列其他通道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优势逐步突显出来,既可承接我国目前仍在高速增长的对欧运输,减轻其他通道的过境压力,又可成为应对某些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应急方案。 同时,在“双循环经济”政策和“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与“中间走廊”沿线各国间的政策沟通,进一步消除障碍、提升共识,创新合作机制,依托中欧班列将跨里海“中间走廊”打造成一条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共生共荣的发展之路,必将进一步提升跨里海“中间走廊”通道的竞争力和吸引力,让这条古丝绸之路、新“中间走廊”在新时代焕发出其内生的魅力和活力。 文章来源: 《学术探索》年第12期,参考注释请参看原文 作者简介:姜明新湖北武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中东问题,土耳其研究。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